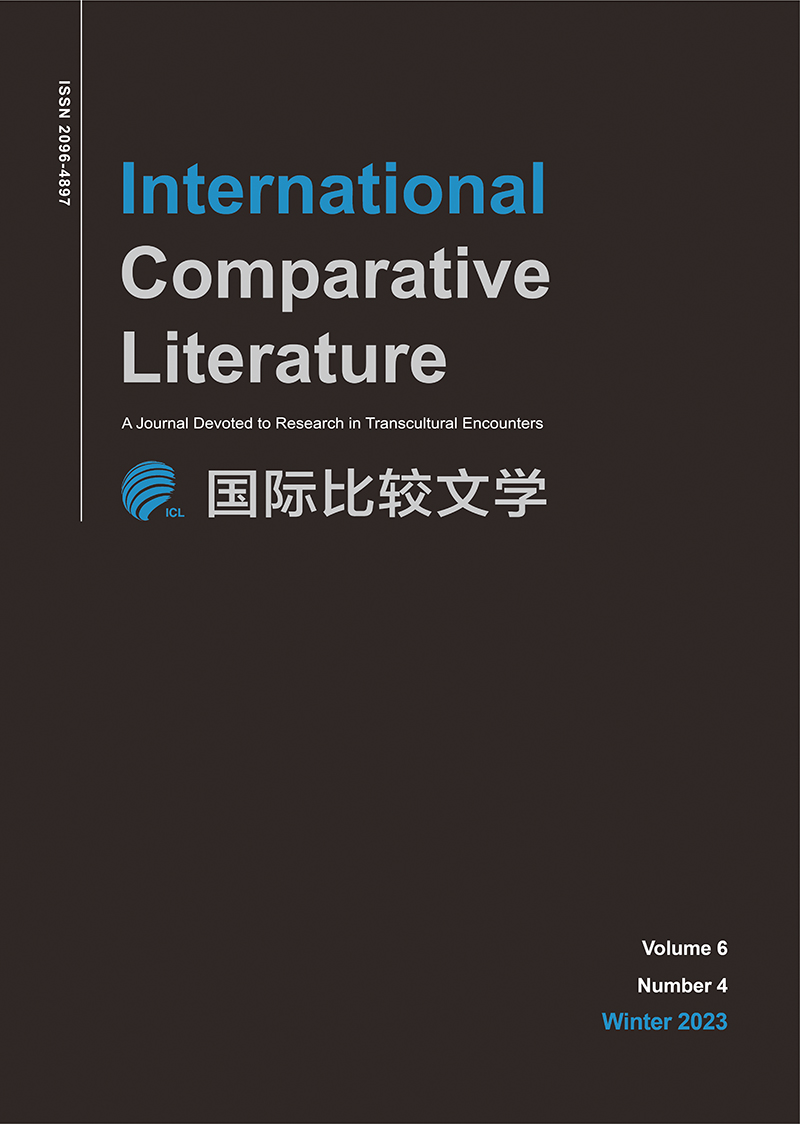2020, 3(4): 729-735.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409
中国文学人类学2018—2020年的研究,延续了该学科跨学科的抱负和开疆拓土的魄力,并在更深的思想意义上重回“中国”立场和“文学”关切,实现了对于本学科核心理论关切的本质回归,“中国”和“文学”得到更立体的理论刻画。中国文学人类学重回“初心”,站定中国立场,展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立意识。
2020, 3(4): 605-635.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401
中国学者中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忠”因有“仁”这一天平的裁量因而是相对的,而日本人的“忠”是无“仁”之“忠”因而是绝对的。本文的考察从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出发,旨在检验此观点关于中国人忠诚观的部分是否成立。考察显示,虽然就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而言该观点成立,然而当我们的视野转向历史文献、《赵氏孤儿》舞台的演变、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忠诚观等诸多方面时,发现该观点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妨碍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学与忠诚观相互交织激烈碰撞的种种现象及本质,因而是极其有害的。然而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却是其鼓吹的如下刻板成见:即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扎根于各自的民族性格之中,从来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观点其实不啻于一个类似“日本人论”的“中国人论”,必须对其加以批判。
2020, 3(1): 179-189.
刊出日期:2021-03-09
2018, 1(2): 287-294.
文学人类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先锋。在经过从文学作品到文学文本、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文本的论域拓展之后,文学人类学进一步向着当代人文学科的思想腹地挺近。借助于对"多重证据"和"物的叙事"的多维观审,文学人类学凸显了当代思想对物之"物性"的再思。文学人类学对物的"重现发现",处在物我关系时代变迁的"合题"阶段,也应和着当代思想的辩证革新。物性再思不仅唤醒物,也开启了物我共生的新世界。
2019, 2(2): 169-205.
刊出日期:2021-03-09
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1731)是第一部西传的中国纯文学著作,1735年杜赫德首先将之收入所编《中华帝国全志》。自此以来,近人如儒莲、艾田蒲、范存忠与今人如伊维德等每诟之。据他们所见,马译舛误颇多,其中最大的一点,厥为马若瑟缺译全剧曲词,且他对中国戏曲所知有限。本文据这些论点重审马译,认为马若瑟读过不少中国传统戏曲,而所谓马译阙译曲词,恐怕也值得商榷。以后者而论,本文认为马若瑟至少透过重编,译过四阙曲牌。他多数曲牌阙译,原因有二︰其一是船期在即,马若瑟仅有七八天可译《赵氏孤儿》,因此来不及如数译之。其次,他有信致当时皇家美文与铭文学院院士傅尔蒙,提及由傅氏补足全文阙译处,即使由傅氏挂名刊出也无妨。至于马若瑟的中国戏曲知识,本文据马著《汉语札记》,认为论者过于轻忽,北曲南戏马若瑟所读不少,前者至少包括《元曲选》中的包公戏、神仙道化剧与水浒剧三类,后者之大者乃《笠翁十种曲》中李渔所谱至少半数的剧目。历来论者对马译的恶评,因此恐有言重之嫌。
2022, 5(2): 181-184.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210
2019, 2(4): 805-807.
刊出日期:2021-03-09
2020, 3(4): 780-783.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416
2022, 5(1): 193-196.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114
2023, 6(4): 39-5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3
西方电影叙述学有把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定性为如戏剧表演那样的演示叙述、而不是记录演示叙述或兼具这两者某些特征的传统。这样理解的根源,在于未能注意到胡塞尔的感知理论无法有效区分幻觉和感知的局限。事实上,戏剧舞台表演等现场演示叙述类型的许多基本特征,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并不具有,不能无视后者经过了媒介录制这个环节的事实,忽视这种媒介性,会面临无法精细有效区分诸多叙述类型的麻烦。无疑,记录性演示叙述具有双重性,即兼具现场演示叙述类型与记录叙述类型的一些特征。另外,学界对演示叙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的讨论,多沿用受限于语言文字中心主义视野的经典叙述学的概念与理论框架,而未完全回到这种体裁本身。演示叙述的创作机制、发生场域、符号-媒介与存在形态等远比小说复杂,其叙述框架发生在两个场域,其框架并非一个,其中一个区隔了故事文本内外,另一个区隔了处于故事文本外却参与了其建构的各种叙述主体的创作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此类区隔本身具有抽象性。同时,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等次叙述者的作用是相对的、变动的,甚至某些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合一,其表演者属于一种用身体、姿态、行为动作等符号直接演述故事的叙述者,而一些画外音等则属于小说叙述意义上的叙述者。
- 首页
- 上一页
- 1
- 2
- 下一页
- 末页
- 共:2页